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自我效能感与促进定向的中介效应
The Influence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on Employee Job Craf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Promotion Focus
-
摘要: 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就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积极影响进行了研究,并对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在其中发挥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剖析。研究结果表明: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员工自我效能感以及促进定向部分中介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挑战性压力源可以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影响工作重塑。本文丰富了工作重塑发生机制的研究成果,为组织管理员工有效应对工作中的压力提供了思路。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on individual job crafting,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self-efficacy and promotion focus. By analyzing 238 questionnaire data collect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hallenging stressors positively affect employees' job crafting; and the self-efficacy of employees and promotion focus partly mediates the influence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on job crafting. This study discusses two different ways that challenging stressors affect individual job crafting, focuses on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hallenging stressors, enriches the mechanism of job crafting, and provides ideas for organizations to effectively manage employees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in work.
-
Keywords:
- challengingstressors /
- self-efficacy /
- promotionfocus /
- jobcrafting /
- Employee work
-
近年来,为了应对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组织内部不得不采取并购重组、流程再造、裁员等一系列变革措施。组织内部变革与外部环境变化给员工带来了挑战,对员工提出了更高的工作要求,外部雇佣环境的变化与不确定性也给员工身心带来双重压力。
Cavanaugh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源进行了界定[1],提出给员工带来积极情绪体验与结果的压力源是挑战性压力源,给员工带来消极结果的压力源则是阻断性压力源。安彦蓉等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的创造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因为压力有时候也是一种动力,能够促使员工保持一定的危机意识,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动力。刘博和赵金金指出,在实际工作中,员工会对工作场所中的工作特征与环境做出评价,进而决定采取何种策略或措施来改变工作特征,避免消极效应的产生[3]。工作重塑是员工应对组织变革和变化的积极手段,可提高员工的持续工作能力,帮助员工响应工作场所的变化[4]。不同于占主导地位的自上而下的工作设计方法,工作重塑是员工的主动性行为,是员工为实现资源与要求平衡自下而上自主采取的调整自身工作特征的行为。工作重塑作为一种主动性行为,是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应对组织变革与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性压力源的有效方式之一。本文拟从工作重塑入手研究员工积极应对挑战性压力源的行为。
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后,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应对目前的挑战,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改变现有的工作特征,将压力化为动力。Stumpf等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感的员工在问题情境中倾向于积极地应对、解决问题[5]。自我效能感作为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很有可能是连接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桥梁。本研究拟探讨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
压力可视为环境与个人特质相互作用的结果[6],积极的压力源能够给个体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从而促使员工在工作场所改变工作态度与行为方式。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何种特质的员工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是本研究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促进定向是源于调节定向理论的个体动机状态。目前调节定向研究大都集中于消费行为领域,较少关注促进定向对员工认知、态度、情绪、身心健康及行为的影响[7],近年来学者们才开始将工作重塑与调节定向理论结合起来[8]。李锐和王怀勇指出,情境因素导致的情境性促进定向的诱发动机和认知处理模式能够使员工在后期的应对过程中倾向于采取趋近策略和争取最大化的积极结果[9]。Tims和Bakker提出,与防御定向的个体相比,促进定向的个体实施工作重塑行为的可能性更大[10]。因此,有必要对挑战性压力源对促进定向的激发作用和促进定向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进行研究。
综上,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主观能动性及压力应对策略的影响,即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的情况下员工个体自我效能感与促进定向的作用;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机制及挑战性压力源的积极影响。
一.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
工作压力是一种由工作或与工作直接有关的因素造成的心理应激,而工作压力源则是引起个体压力感知的刺激前提[11,12]。Cavanaugh等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压力源进行了界定。他们提出:挑战性压力源是指被个体感知为奖励的工作要求,包括时间压力、工作负荷、高工作责任、高学习要求等。这类压力源产生的压力能被克服,且一旦克服就能给员工带来物质及精神上的收益与回报。阻断性压力源是指被个体感知为成长障碍,对个人目标达成造成干扰或者对个人工作能力形成限制的一系列工作要求,包括角色模糊、组织政治、工作不安全感等。这类压力源产生的压力很难被克服,且个体无法从中获益[1]。不同性质的压力源会对员工的态度与行为产生差异性影响。阻断性压力源会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导致个体采取消极的应对策略。张勇等研究发现阻断性压力源通过自我效能负向影响员工创造力[13]。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行为。杨皖苏等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可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支持感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创新行为[14]。
Wrzesniewski和Dutton将工作重塑界定为员工为使自身兴趣、动机以及热情等与工作一致,在工作场所自我激发的一系列改变工作认知、任务和关系的行为[15]。Tims和Bakker以JD-R模型(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为理论基础,将工作重塑定义为“员工为实现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的平衡,根据自身能力与需求做出的主动改变”[10]。从上述概念可以看出,工作重塑是员工在工作场所自发采取的主动改变行为。Wrzesniewski和Dutton指出,实现自我控制、树立积极自我形象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这三种基本个人需求是激发工作重塑的重要因素[15]。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的情况下,为保持稳定的情绪,实现对工作的控制,员工会采取一系列主动性行为,以改变工作的各个方面。刘淑桢等研究发现,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期望能够保持持续的工作能力、提高职业胜任能力以及获得持续性组织收益的员工会产生改变工作特征的行为,以便在应对压力的同时向他人展示积极的自我形象,即采取重塑现有工作特征的行为[16]。Harju等研究发现挑战性的工作要求可以减少个体的工作倦怠,进而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17]。刘云等研究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可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进而增强员工的工作幸福感[18]。陈春花等基于自我决定理论进行研究后发现,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员工任务重塑行为,进而激发个体的创新行为[1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
二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Bandura指出个体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特定目标,相信自己能够成功做成某件事的主观感知[20]。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说服是激发个体自我效能感的外部来源之一。挑战性压力源对应的工作要求会让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以及上级的重视、信任与期待,会被员工感知为“社会说服”,从而促进员工自我效能感的提升[21]。个体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且认为自己有能力应对压力时,会激发自我效能感,表现出积极主动的行为。员工自身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积极应对压力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2: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
Lazarus的认知评价理论指出员工对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对自身能力的认知评价将影响其压力应对行为[22]。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是连接外在环境与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13];自我效能感是动机的核心影响因素之一,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更愿意采取问题导向式的、积极的应对方式[23]。张亚军和肖小虹研究证实,挑战性压力源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员工创造力[24]。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个人控制感会更强,这种控制感有助于个体在感知压力时产生战胜压力的信心,进而促使个体产生更多的主动性行为[25]。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目前的挑战,倾向于采取提高工作控制力、重塑自我形象、积极建立联系等主动应对措施,能够促进工作重塑行为产生,有助于自身主动将压力转化为动力。相反,自我效能感低的个体认为自己无法战胜来自组织内外部的压力,不能完成高工作要求,无法克服困难,因此不太可能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邓春平等认为挑战性压力源产生的刺激会激励员工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以避免压力带来的消极影响[26]。张勇等基于社会认知角度证实挑战性压力可通过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激发员工的创造力[13]。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三 促进定向的中介作用
促进定向源于调节定向理论,促进定向的个体关注成长、需求、成就等积极结果,趋近积极的目标状态,对积极结果的出现与缺失敏感,易表现出积极主动性行为[27]。促进定向既可以是受个人特质倾向影响形成的长期特质,也可以是受情境因素或任务影响形成的一种短期状态。有学者指出,重视成长、收获与理想的工作环境能够激发员工的情境性促进定向[7]。当个体所处的环境能够引导其促进定向形成时,那么员工就有可能成为促进定向的个体。例如,变革型领导关注下属成员的进步与发展,鼓励员工成长,为员工追求理想状态与积极目标提供支持性氛围,能够激发员工促进定向的形成[28]。挑战性压力源作为组织情境与个体相互作用的因素,被员工感知为奖励性工作要求,强调员工的成长与进步,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的促进定向状态。所以,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的促进定向。
韩强指出当员工感受到情境因素变化时,促进定向的员工有清晰的目标导向,能激发自身强烈的内在动机,进而会为了实现工作目标、提高胜任能力等积极结果而不断提升自我[29]。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会趋向于改变目前的压力状态,自发地采取工作重塑等积极措施来应对压力。Petrou和Demerouti发现情境性促进定向能够激发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包括寻求资源与挑战[30]。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关注成长与积极结果。他们会认为挑战性压力源能给自己带来成长,会积极地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来应对挑战性压力,容易产生工作重塑行为[3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5: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所有假设,本研究构建理论模型,见图1。
二.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
本次调查发放问卷274份,剔除填写有明显规律以及填写时间过短的问卷36份,最终有效问卷为238份,回收有效率为86.8%。从性别来看,男性与女性比例相差不大;从年龄来看,研究样本以21~25岁和26~30岁为主;在受教育程度这一项,本科学历占47.1%;从岗位级别来看,调查对象主要是普通员工。具体样本信息见表1。
表 1 研究样本基本信息统计项目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98 41.2 女 140 58.8 年龄 20岁及以下 24 10.1 21~25岁 56 23.5 26~30岁 67 28.2 31~35岁 39 16.4 36~40岁 32 13.4 41岁及以上 20 8.4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2 13.4 专科 67 28.2 本科 112 47.1 研究生及以上 27 11.3 工作年限 1年以下 57 23.9 1~3年 32 13.4 3~5年 65 27.3 5~10年 59 21.0 10年以上 43 14.3 岗位级别 普通员工 139 58.4 基层管理者 56 23.5 中层管理者 25 10.5 高层管理者 18 7.6 二 变量测量
本次问卷调查使用的是国内外相关研究中较为成熟的量表。同时,为便于被试者理解,研究根据具体的使用情境对量表中一些措辞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1)挑战性压力源的测量采用Cavanaugh等[1]开发的量表。量表中测量挑战性压力源的条目共有6个,“1”代表“完全没压力”,“5”代表“非常有压力”。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39。
2)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采用Schwarzer等[32]开发的GSES量表。量表共10个测量题项,“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60。
3)促进定向的测量采用Neubert等[33]的工作调节焦点量表(WRF)。量表中测量促进定向的条目共有9个,“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27。
4)工作重塑的测量采用Petrou等[34]开发的量表。量表中测量资源找寻的条目有6个,其中3个题项用于测量挑战寻求,4个题项用于测量需求减少,“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本次测量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85。
5)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性别、年龄、工作年限、受教育程度以及岗位等级。根据Rudolph等人[31]的分析,上述背景变量会对工作重塑产生影响。
三.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分析法检验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的最大因子累积解释方差为31.344%,说明不存在单一因子解释绝大部分变异的情况。因此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符合要求。
二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显著性水平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正相关(r=0.479,p<0.01),与自我效能感正相关(r=0.539,p<0.01),与促进定向正相关(r=0.525,p<0.01)。从表2还可以看出,自我效能感与工作重塑正相关(r=0.795,p<0.01),促进定向与工作重塑正相关(r=0.834,p<0.01)。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1 年龄 −0.184** 1 受教育程度 0.131* −0.103 1 工作年限 −0.103 0.691** −0.187* 1 岗位等级 −0.137* 0.189** −0.146* 0.334* 1 挑战性压力源 −0.095 0.258** −0.052 0.280** 0.161* 1 自我效能感 0.083 0.138* −0.014 0.205** 0.114 0.539** 1 促进定向 0.101 0.044 0.031 0.083 0.093 0.525** 0.842** 1 工作重塑 0.175** 0.008 0.035 0.067 0.021 0.479** 0.795** 0.834** 1 平均值 1.590 3.250 2.560 2.880 1.670 2.973 3.254 3.247 3.319 标准差 0.493 1.430 0.863 1.367 0.942 0.929 0.828 0.838 0.818 注:**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三 假设检验
本文采用SPSS20.0统计分析软件,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分别对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3。
表 3 回归结果分析变量 自我效能感 促进定向 工作重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性别 0.190 0.231 0.198 0.241 0.297** 0.336*** 0.167 0.152 年龄 0.012 −0.025 0.003 −0.035 −0.020 −0.055 −0.037 −0.028 受教育程度 0.017 0.013 0.041 0.036 0.030 0.026 0.016 −0.002 工作年限 0.112* 0.057 0.042 −0.016 0.065 0.012 −0.030 0.024 岗位级别 0.058 0.022 0.081 0.043 0.018 −0.017 −0.033 −0.050 挑战性压力源 0.475*** 0.500*** 0.460*** 0.111** 0.077* 自我效能感 0.734*** 促进定向 0.765*** R2 0.057 0.315 0.028 0.306 0.040 0.287 0.665 0.712 △R2 0.057 0.257 0.028 0.279 0.040 0.247 0.378 0.425 F 2.822* 17.665*** 1.316 17.000*** 1.927 15.467*** 65.215** 81.20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1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由模型6可知,在排除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的工作重塑行为(β=0.460,p<0.001),H1得到支持。其次检验挑战性压力源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由模型2可知,挑战性压力源对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0.475,p<0.001),H2得到支持。最后将挑战性压力源与自我效能感放入工作重塑回归方程。由模型7可知,自我效能感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β=0.734,p<.0.001),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β=0.111,p<0.01),但系数有所下降,说明员工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中有部分中介作用,H3得到支持。
2 促进定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1)模型6的结果显示H1得到支持,即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由模型4可知,挑战性压力源对促进定向有显著正向影响(β=0.500,p<0.001),H4得到支持。3)将挑战性压力源与促进定向放入工作重塑回归方程,由模型8可知,促进定向正向影响工作重塑(β=0.765,p<0.001),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显著(β=0.077,p<0.05),但系数有所下降。这说明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H5得到支持。假设验证的结果见表4。
表 4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 H1: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 成立 H2: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 成立 H3: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H4: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促进定向 成立 H5: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挑战性压力源对员工工作重塑的影响,以及自我效能感和促进定向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为了实现对工作的控制、获得持续性职业收益以及向他人展示积极的自我形象,员工会在挑战性压力源的激励下产生一系列改变目前工作的主动性行为,即工作重塑。2)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正向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自我效能感高的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压力,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促进了工作重塑行为的产生。3)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的正向关系中有部分中介作用。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关注成长与积极结果。他们会认为挑战性压力源能给自己带来成长,因此会积极地增加社会性工作资源来应对挑战性压力,更容易产生工作重塑行为。
二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关注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的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了促进定向与工作重塑关系研究成果。其次,以往的研究大都直接探讨压力源(包括挑战性压力源与阻断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直接影响,本研究探讨了自我效能感与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证明挑战性压力源可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影响工作重塑,丰富了工作重塑发生机制的研究成果。
三 管理启示
第一,挑战性压力源能够激发员工主动性工作重塑行为,因此,组织应注意区分压力源的性质。对此,组织可以营造适当的压力氛围,增加一些奖励性的、积极的工作要求与体验,通过适当的挑战性压力源来激发员工的主动性;引导员工合理地看待压力,培养员工积极应对压力的意识。
第二,在面对挑战性压力源时,组织或领导可以通过奖励、表扬、信任,必要时适当授权等措施激发员工的自我效能感,让员工相信自己有能力面对工作中的挑战性压力源带来的压力,促使员工去积极应对。通过这些举措使压力转化为动力,激发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员工产生工作重塑行为。
第三,在感知到挑战性压力源时,促进定向的个体更容易激发自身的工作重塑行为。组织要积极引导并激励员工形成促进定向状态,关注员工的进步、发展和成就等需求,并且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积极反馈,营造积极的、能够激发员工促进定向的文化氛围。
四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首先,本文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有待深入验证,后续研究可采取纵向跟踪分析方式,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其次,本研究探讨的是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整体影响,未来可对不同维度的具体影响进行探讨。最后,本研究未涉及挑战性压力源影响员工工作重塑的边界条件。刘博和赵金金发现挑战性压力源对工作重塑的影响受到人—工作匹配的调节,高人—工作匹配的员工在面临适度的挑战性压力时更容易产生工作重塑行为[3]。所以未来可对不同的个体间该影响的差异或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下该影响的差异进行探讨。
-
表 1 研究样本基本信息
统计项目 样本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98 41.2 女 140 58.8 年龄 20岁及以下 24 10.1 21~25岁 56 23.5 26~30岁 67 28.2 31~35岁 39 16.4 36~40岁 32 13.4 41岁及以上 20 8.4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32 13.4 专科 67 28.2 本科 112 47.1 研究生及以上 27 11.3 工作年限 1年以下 57 23.9 1~3年 32 13.4 3~5年 65 27.3 5~10年 59 21.0 10年以上 43 14.3 岗位级别 普通员工 139 58.4 基层管理者 56 23.5 中层管理者 25 10.5 高层管理者 18 7.6 表 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性别 1 年龄 −0.184** 1 受教育程度 0.131* −0.103 1 工作年限 −0.103 0.691** −0.187* 1 岗位等级 −0.137* 0.189** −0.146* 0.334* 1 挑战性压力源 −0.095 0.258** −0.052 0.280** 0.161* 1 自我效能感 0.083 0.138* −0.014 0.205** 0.114 0.539** 1 促进定向 0.101 0.044 0.031 0.083 0.093 0.525** 0.842** 1 工作重塑 0.175** 0.008 0.035 0.067 0.021 0.479** 0.795** 0.834** 1 平均值 1.590 3.250 2.560 2.880 1.670 2.973 3.254 3.247 3.319 标准差 0.493 1.430 0.863 1.367 0.942 0.929 0.828 0.838 0.818 注:**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表 3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自我效能感 促进定向 工作重塑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性别 0.190 0.231 0.198 0.241 0.297** 0.336*** 0.167 0.152 年龄 0.012 −0.025 0.003 −0.035 −0.020 −0.055 −0.037 −0.028 受教育程度 0.017 0.013 0.041 0.036 0.030 0.026 0.016 −0.002 工作年限 0.112* 0.057 0.042 −0.016 0.065 0.012 −0.030 0.024 岗位级别 0.058 0.022 0.081 0.043 0.018 −0.017 −0.033 −0.050 挑战性压力源 0.475*** 0.500*** 0.460*** 0.111** 0.077* 自我效能感 0.734*** 促进定向 0.765*** R2 0.057 0.315 0.028 0.306 0.040 0.287 0.665 0.712 △R2 0.057 0.257 0.028 0.279 0.040 0.247 0.378 0.425 F 2.822* 17.665*** 1.316 17.000*** 1.927 15.467*** 65.215** 81.203***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双尾检测)。 表 4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研究假设 研究结果 H1: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工作重塑 成立 H2: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自我效能感 成立 H3:自我效能感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H4:挑战性压力源正向影响员工促进定向 成立 H5:促进定向在挑战性压力源与工作重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成立 -
[1] CAVANAUGH M A, BOSWELL Wendy R, ROEHLING Mark V, et al.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self-reported work stress among US manager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 85(1): 65 − 74. doi: 10.1037/0021-9010.85.1.65
[2] 安彦蓉, 杨东涛, 刘云.化压力为创新: 上级发展性反馈与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 2-8(2020-03-30)[2020-12-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00327.1711.018.html. [3] 刘博, 赵金金. 挑战性压力与工作重塑的曲线关系——促进聚焦和人—工作匹配的作用[J]. 软科学,2019,33(6):121 − 125. [4] KIRA M, EIJNATTEN F M V, BALKIN D B. Crafting Sustainable Work: Development of Personal Resource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 2010, 23(5): 616 − 632. doi: 10.1108/09534811011071315
[5] STUMPFS S A, BRIEF A P, HARTMAN K. Self-efficacy expectations and coping with career-related event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1987(31): 91 − 108.
[6] DECI E L, RYAN R M.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human behavior[J].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4, 3(2): 437 − 448.
[7] 毛畅果. 调节焦点理论: 组织管理中的应用[J]. 心理科学进展,2017,25(4):682 − 690. [8] 田喜洲, 郭小东, 许浩. 工作重塑研究的新动向——基于调节定向的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2020,28(8):1367 − 1378. [9] 李悦, 王怀勇.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优势匹配感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16):148 − 154. doi: 10.6049/kjjbydc.2016100048 [10] TIMS M, BAKKER A B. Job crafting: Towards a new model of individual job redesign[J]. Journal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2010, 36(2): 1 − 9.
[11] LEPINE J A, PODSAKOFF N P, LEPINE M A. A Meta-analytic Test of the Challenge Stressor-hindance Stressor Framework: An Explanation for Inconsistent Relationships Among Stressors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48(5): 764 − 775. doi: 10.5465/amj.2005.18803921
[12] 李宗波, 李锐.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源研究述评[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13,35(5):40 − 49. [13] 张勇, 刘海全, 王明旋,等. 挑战性压力和阻断性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 自我效能的中介效应与组织公平的调节效应[J]. 心理学报,2018,50(4):450 − 461. [14] 杨皖苏, 杨希, 杨善林. 挑战性压力源对新生代员工主动性—被动性创新行为的影响[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8):139 − 145. [15] WRZESNIEWSKI A, DUTTON J E. Crafting a Job: Revisioning Employees as Active Crafters of Their Work[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1, 26(2): 179 − 201. doi: 10.5465/amr.2001.4378011
[16] 刘淑桢, 叶龙, 郭名. 工作不安全感如何成为创新行为的助推力——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的研究[J]. 经济管理,2019,41(11):126 − 140. [17] HARJU L K, HAKANEN J J, SCHAUFELI W B. Can job crafting reduce job boredom and increase work engagement?a three-year cross-lagged panel study[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6, 95-96: 11 − 20. doi: 10.1016/j.jvb.2016.07.001
[18] 刘云, 杨东涛, 安彦蓉.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与工作幸福感关系研究: 基于工作重塑的中介作用[J]. 当代经济管理,2019,41(8):77 − 84. [19] 陈春花, 廖琳, 李语嫣, 等. 有压力才有动力: 挑战性压力源对个体创新行为的影响[J/OL]. 科技进步与对策.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00721.1140.032.html [20] BANDURA A, LOCKE E A. Negative self-efficacy and goal effects revisited[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1): 87 − 99. doi: 10.1037/0021-9010.88.1.87
[21] PREM R, OHLY S, KUBICEK B, et al. Thriving on challenge stressors? Exploring time pressure and learning demands as antecedents of thriving at work[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7, 38(1): 108 − 123. doi: 10.1002/job.2115
[22] LAZARUS R S. From psychological stress to the emotions: A history of changing outlook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1993(44): 1 − 21.
[23] 杨柳青, 梁巧转, 赵欣. 压力与学习的互惠: 对积极塑造者假说的纵贯实证检验[J]. 科技管理研究,2014,34(21):116 − 121.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4.21.024 [24] 张亚军, 肖小虹. 挑战性—阻碍性压力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研究[J]. 科研管理,2016,37(6):10 − 18. [25] SIU O, SPECTOR P E, COOPER C L, et al. Work Stress, Self-Efficacy, Chinese Work Values and Work Well-Being in Hong Kong and Beij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2005, 12(3): 274 − 288. doi: 10.1037/1072-5245.12.3.274
[26] 邓春平, 刘小娟, 毛基业. 挑战与阻断性压力源对边界跨越结果的影响——IT员工压力学习的有调节中介效应[J]. 管理评论,2018,30(7):150 − 163. [27] 曹元坤, 徐红丹. 调节焦点理论在组织管理中的应用述评[J]. 管理学报,2017,14(8):1254 − 1262. doi: 10.3969/j.issn.1672-884x.2017.08.017 [28] 李渊, 曲世友, 徐峰. 变革型领导力与员工创新行为模式: 基于促进定向的中介作用[J]. 中国软科学,2019(7):125 − 133. doi: 10.3969/j.issn.1002-9753.2019.07.012 [29] 韩强. 调节焦点、绩效考核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J]. 经营与管理,2013(9):91 − 93. [30] PETROU P, DEMEROUTI E. Trait-level and week-level regulatory focus as a motivation to craft a job[J]. Career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2015, 20(2): 102 − 118. doi: 10.1108/CDI-09-2014-0124
[31] RUDOLPH C W, KATZ I M, LAVIGNE K N, et al. Job crafting: A meta-analysis of relationships with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ob characteristics, and work outcome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17, 102(10): 112 − 138.
[32] SCHWARZER R, BABLER J, KWIATEK P, et al. The Assessment of Optimistic Self-beliefs: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Span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J]. Applied Psych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1997, 46(1): 69 − 88. doi: 10.1111/j.1464-0597.1997.tb01096.x
[33] NEUBERT M J, KACMAR K M, CARLSON D S, et al. Regulatory Focus as A Mediator of the Influence of Initiating Structure and Servant Leadership on Employee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8, 93(6): 122 − 123.
[34] PETROU P, DEMEROUTI E, PEETERS M, et al. Crafting a job on a daily basis: Contextual antecedents and the link to work engagement[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2, 33(8): 1120 − 1141. doi: 10.1002/job.1783
-
期刊类型引用(1)
1. 蔡诗雨,杨柳. 提升现代工作场所乐趣的途径——以工作重塑干预为视角. 市场周刊. 2021(08): 150-152 .  百度学术
百度学术
其他类型引用(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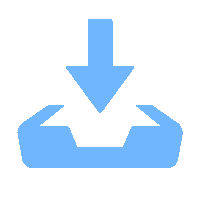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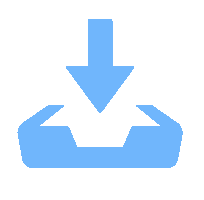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