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勋古韵学述略
A Study on Ancient Rhymes by Zou Hanxun
-
摘要: 邹汉勋的古韵研究以传统哲学中的“数理”思想为指导,分古韵为正韵十五类,另有入声十部属之。邹氏正韵十五类与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高度密合,其间传承关系颇为明显;在入声韵部的处理上邹与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大为不同。邹氏开启了参酌方音以求古韵部音值的先河,他对语音演变的认识已有离散式音变理论的萌芽;然而,邹氏狃于南楚方音,推求古韵音值的过程中,失当之处不少。Abstract: The study on ancient rhymes by Zou Hanxun is based on the mathematical ideology from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it classifies the ancient rhymes into fifteen types of basic rhymes and ten types of entering tones. The fifteen types of basic rhymes by Zou have a high degree of unity with the seventeen types of ancient rhymes by Duan Yucai. The relationship of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m is quite obvious, but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rhymes of entering tone, Zou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Gu Yanwu, JiangYong, DaiZhen and DuanYucai. Zou Hanxun pioneers to get the sound of ancient rhymes, referring to dialects, and his awareness of pronunciation changes reveals an embryo of the theory of dispersive phonetic change in western countries. However, being restricted to the Nancu dialect, the study on ancient rhymes by Zou made many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deriving the sound of ancient rhymes.
-
邹汉勋(1805—1854),字叔绩,清代著名学者,湖南新化(今属隆回)人。咸丰元年(1851)中举,是我国近代史上杰出的舆地学家,中国近代舆地学奠基人。邹汉勋一生著述丰富,主要有《五均论》、《读书偶识》、《水经移注》等30余种,共460余卷,多毁于兵燹战乱,后人刊有《邹叔子遗书》七种传世。邹氏兄弟六人,少蒙庭训,皆以才称,而汉勋为最。邹氏博学多才,被士林尊称为“古之郑贾,今之江戴”①。他与当时名动京华的魏源以及大书法家何绍基并称为“湘中三杰”。
邹氏音韵学著作凡五种:《说文谐声谱》十六卷、《广韵表》十卷、《五韵表》十卷、《五均论》二卷、《二十二字母考》五卷。前两种在编刻遗书时,表谱已残,叙言收在遗书文存内,唯有《五韵论》得以比较完整地保留。《五韵论》作于咸丰元年(1851),是邹氏最后之音韵著作。此书为系统阐述邹氏自己的古韵体系(古声二十纽与古韵十五部)及立论理由而作,故议论少而例证多。
一般认为,章太炎是第一个对古声纽有系统认识的人②。实际上,邹氏“古声二十纽”之说自成体系,较章氏“古声二十一纽”说为早。章氏的古声学说,乃东渡扶桑以后,在研习梵文、遍览诸说并考核《说文》的基础上形成的。1907年,《古音娘日二妞归泥说》与《古双声说》的发表,标志着章氏古声体系的成熟,此时距邹氏古声二十纽体系的形成,已逾半个世纪。邹氏的古声学说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巨。黄侃所著《古韵谱稿》扉页有其本人亲笔:“十九声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廿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群。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及番禺陈君(陈澧)而成,不可匿其由来也。”
除系统的古声纽理论外,邹氏也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古韵体系。《五均论下·十五类三十论》集中展示了他的古韵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 古韵十五部的划分
李登《声类》、吕静《韵集》被邹汉勋认为是保存古韵的代表作品。“李登撰《声类》以五声命字,不立诸部,吕静仿左校令李登之法作《韵集》五卷,宫商角徵羽各为一篇。案李、吕之时,未以氐卬上去入分篇,则其所谓宫商角徵羽必均类也。如是则均类宜可以五尽,五而三之至于十五止矣”[1]289。邹氏所谓“五而三之”,即宫商角徵羽这五类再各分为上中下三类。于是,共得古韵正音十五部,兹胪列如表 1。
表 1上、急 中、缓 下、急 疾徐 宫 鱼模 歌戈麻 支佳 商 阳唐谈盐添严衔咸 东冬钟江侵覃凡 耕清青 角 真臻先 元寒桓删先 谆文欣魂痕 徵 脂皆 蒸登灰微 之咍齐 羽 宵萧肴豪 侯虞 尤幽 表 1中所陈“上中下”以及“缓急”,究竟以何标准分类而得,邹氏语焉不详。将邹汉勋与顾炎武、江永、段玉裁、戴震四位古音学大家的古韵分部作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异同点:
(1) 顾、江二人将脂之微齐佳皆灰咍八韵合为一部,段、戴二人则将之咍合为一类,脂韵归入另一类,邹汉勋的分部方法正与段、戴相同。
(2) 顾氏将鱼虞模侯归为一类,萧宵肴豪幽尤半划归为另一类。江永以鱼模为一类,虞韵的部分字属之,并将萧宵肴豪两分,一部分自成一类,别一部分字与尤半侯幽以及部分虞韵字合并而成尤侯幽类。戴震基本上继承江永的分法,鱼虞模一类,萧宵肴豪一类,尤侯幽一类。段玉裁与此三人大不同之处在于将侯部独立。邹汉勋的古韵分部与段玉裁最为接近,区别只是将虞韵与侯韵合为一类。因此,顾氏的两类,到江永、戴震手中分为三类,再经段、邹二人离析而成四类。
(3) 顾氏将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归为一类,江永将其两分,真谆臻文殷魂痕先半为一类,元寒桓删山仙先半为另一类。戴震在划定七类二十部时,依从顾氏的分部。至晚年划定九类二十五部时则基本依从江永的分法,只是不再将先韵两分而已。相较于前三者,段玉裁分部愈密,他将江、戴二人的真谆类两分,真臻先为一类,谆文殷魂痕为另一类。邹汉勋的分部方法同段氏。
(4) 顾、江二人都以歌戈为一类,并且都将麻半支半归入此类。段玉裁将歌戈麻归为一部,支韵独立而成支佳部。戴震受段玉裁影响,亦如此分部,邹汉勋的分部与段、戴二人完全相同。
(5) 顾江戴段四人皆以蒸登为一类,而邹氏的蒸登类中还包括灰微韵。
(6) 顾、江二人将阳唐和庚之半归为一类,戴段则以为阳唐为一类,将庚韵归入耕清青一类。邹氏的分部方法与戴、段基本相同,所异之处只在两点:邹氏的阳唐类和耕清类皆不辖庚韵,其它十三类亦如此,这或许是邹氏撰文或后人刊行过程中脱漏所致; 邹氏的阳唐类还包括谈盐添严衔咸六韵。
(7) 顾氏将侵以下九韵归为一类,江氏将其两分。戴震七类二十部中与顾氏同,晚年论定九类二十五部时参考江永意见,将“侵”以下九韵分为两类:侵盐添一类,覃谈咸衔严凡一类,戴氏晚年的分法与段玉裁同。邹汉勋则未将侵以下此九韵另立韵部,侵覃凡与东冬归并为一类,谈盐添严衔咸与阳唐归并为一类。
综上所述,邹汉勋的古韵十五部与段玉裁古韵十七部高度密合,主要区别仅在于邹氏附侵覃凡与东冬钟江,附谈盐添严衔咸于阳唐,因此比段氏少了两部。邹氏的古韵体系乃继承金坛段氏而来,应属较为确定的论断。
邹氏的古韵体系除正韵十五部之外,另有入声十类。邹氏将入声十类配入正韵十五类之中,处于附属地位,这与一般意义上的考古派做法相同。邹氏古音体系中舒声与促声相配情况如下:
宫类:铎部配鱼模陌部配支佳歌麻部无入声相配
商类:葉部配阳唐屋部配东侵耕清部无入声相配
角类:质栉配真先曷祭配元寒谆文部无入声相配
徵类:术缉配脂微职德配之咍蒸登部无入声相配
羽类:葉部配宵豪屋沃配尤幽侯虞部无入声相配
段玉裁的古音体系中,阳唐与鱼虞模同入,歌戈麻与支佳同入。戴震对段氏的分部作了纠正,以铎韵配歌、鱼两部,以陌麦昔锡配庚耕清青和支佳。邹氏以陌部隶支佳,歌麻无入声相配,以铎部隶鱼模、葉部隶阳唐,与戴段皆不相同。
以屋之半与沃韵配尤幽,江永首倡,戴震仍之,邹汉勋与江、戴同。戴震以质术栉物迄为脂微齐灰的入声,以职德屋半为之咍的入声,邹汉勋则将质术两分,质栉配真先,术缉配脂微。
江永以药锡配萧部(宵萧肴豪),戴震以药部配萧部,以今天的学术水平观照之,二人的分配方法亦属大致正确,而邹汉勋以葉之半配宵萧肴豪,颇为怪异。
邹氏正韵十五部的划分,基本同段玉裁。而入声十部的归属,则与顾、江、戴、段四人颇为不同,从考古与审音两个角度观照,失当之处都不少,邹氏在入声韵部的处理上,显示出很大的主观性、随意性。
邹氏论古音,以“数理”导夫先路。他认为:“夫五音咸生于数”、“十五类声音广陕(狭)合数。”[1]293-294基于这种观念,只有当入声为十部而非其它数目时,才能与正韵十五类相配整齐,形成五五二十五声的谐和局面。清代的古音学家,自戴震起,便自觉追求古音系统格局的完备。邹氏踵武前贤,值得称道。但与戴震相比,邹氏的古韵研究以“音有定数”的思想为指导,脱离语言事实,所得出的古韵正韵十五类、入声十类的结论,先验成份较多,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及主观主义色彩。
二. 古韵部音值考订
周祖谟评价戴震与邹汉勋的古韵分部时云:“其说(按:指戴说)大体不误。惟支佳一类之说,之咍一类之说,真谆寒桓一类之说,以言汉魏以上则可,以言隋唐以下则非。邹氏第守其藩篱,而不知古今音韵之流变,聊为附和之言耳。” [2]515明代陈第便已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的历史语音观,在清季,这种观点已广为古音学家所接受。戴震曾明确提出“音之流变有古今”,并进一步指出古今音的流变是有规律的,比如上古甲韵的部分字在中古变入乙韵,往往全族迁徙,到了乙韵则聚族而居。这种全族迁徙、聚族而居的变化方式,即戴震所云“声类大限无古今”。以现代语言学观点审视,戴震不仅承认音变,并且已经描绘出连续式音变的图景。邹氏对戴震“声类大限无古今”的观点提出异议,并且从自己方言中一些不规则音变现象入手拟测古韵部音值(详见第二节),他的这一做法或可以视为离散式音变思想的萌芽。戴震与邹汉勋不仅接受了历史语音观,而且已经开始寻找、归纳历史音变的方式,清儒在古音研究科学化、理论化道路上的孜孜追求值得钦佩。
对于邹汉勋在古韵部音值考订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钱玄同评价颇高:“古音分部既与后世不同,则其各部之音读自应有异,此本极应研究者。然清代的古音学者,对于古韵之音读,多数皆以现代官音读《广韵》之音为准……邹叔绩作《五韵论》,始参考方音以求古韵之音读,颇有可采之处。” [3]177
《十五类卅论》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条分别讨论支佳部、侵覃葉三部、耕清青部以及蒸登部古读。
邹氏认为:支佳部乃全韵俱变之部,古今读音殊异,故难定音。从麻韵“卦佳”二字中,邹氏窥得支佳部古读。“今天下雅读,‘八卦’古化切无作‘八怪’,‘佳古牙切人’无读‘皆人’、‘街人’者。此唐以前之古音,编《切韵》、《唐韵》时尚如此也,盖麻之全部,古读及《切韵》、《唐韵》皆从歌戈,而今麻部之声即唐以前支佳部之声” [1]295。
“卦佳”中古属佳韵,与麻韵字主元音相同,唯多出元音韵尾-i。至近代,“卦佳”等字元音韵尾脱落,于是读同麻韵,从而与其它佳韵字有别[4]93-98。邹氏不明语音历史演变规律,狃习方音,于是误将麻韵今读作为支佳部古读。
另外,邹氏对麻韵字的古读,判断亦不准确。中古麻韵字,上古两属。半属鱼部,如“家巴”等,半属歌部,如“加差麻蛇”等。邹氏认为麻韵上古及中古读音皆从歌戈,有误。鱼部之麻与歌部之麻大约在汉代才合流,先秦俨然有别。
《十五类卅论》第十八论,邹氏重点探讨闭口韵的问题。江永《四声切韵表》云:“侵寝沁缉以后九类三十六部列于均末,词曲家谓之闭口音,细审之亦不甚合,今从旧标开口,此皆开口无合者也。”侵缉诸韵为闭口韵,是前贤从韵尾的角度审音得出的结果,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分析,闭口韵即收-m尾的韵。江氏从介音的角度来分析词曲家所谓闭口韵,混同“合口”与“闭口”,得出了错误结论——闭口韵本应属于开口。邹汉勋列举《七音略》、《淮南音》、《唐韵》、邵雍《观物外篇》诸书之中的例子,以证明江永所言误甚。然而,邹氏自己分析闭口韵的角度也未为妥当。
戴震《答段若膺论韵书》云:“侵以下九韵皆收唇音,其入声古今无异说。方之诸均,声气最敛,词家谓之闭口音。”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来看,戴震的分析至为精当。这一方面与他长于审音有关,另一方面,在戴氏生活的时代,浙东地区可能尚有闭口韵孑遗[5]。麦耘先生认为:汉语共同语北支中的-m韵尾(即闭口韵韵尾)的消变时限在16世纪晚期,而在共同语南支中,消变的上限为18世纪中叶,下限待考[6]。戴震移居浙东恰好在18世纪中叶,得天独厚的方言条件使他更容易对闭口韵的读音做出正确判断。
邹氏对戴说的理解,明显属于郢书燕说。邹氏云:“此说(即戴说)闭口韵又与江慎修异,殆不在八等之中求开闭,但以均比较,诸均皆大,而此部独敛为闭口耳,其说似确,但不知其读之也如何。党仍不离真先之音邪?则真先之音,不大不细,不可谓之独敛。且大判与真先同,亦不宜分而二之。” [1]296-297也许因为邹氏不具备戴震那样的方言背景,所以只能从元音侈敛的角度来分析闭口韵。侵覃与真先,主元音相同(或极相近),因此邹氏只能得出“且大判与真先同,亦不宜分而二之”的结论。
从谐声材料的角度分析,侵覃诸韵有通豪尤幽者。邹氏认为,侵覃诸均“倘读同尤幽豪,则真敛矣”,然而亦当与豪萧宵肴尤幽同为一类,不必另立名目曰闭口韵。因为“闭口之说,原出周德清,于前无闻,不以之与均法相纠缠,亦廓清均部之一功也” [1]296-297。
豪萧诸韵,收元音韵尾-u,发音时确有合唇动作,然而这与侵覃诸韵收辅音-m尾有着质的区别。邹氏既不能挣脱方音桎棝,亦不克详审等韵著作以明辩深咸二摄与臻山、效流诸摄之别,所以始终无法䌷绎出闭口韵的区别特征,进而得出“闭口韵古无是说不可从”的错误结论,诚为憾事。
方音虽然在剖判闭口韵时误导了邹汉勋,却在考订耕清青旧音时为他提供了便利,亦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耕清青之旧音近于阳唐,夫人而知之矣。乃今之雅读,无一不合于真臻欣先” [1]300。邹氏所谓雅读,大约是指当时的长沙话。在邹氏自己的方言中,耕清青读音与真臻欣先迥异。“余生长南楚,南楚鄙人于庚耕清青四均无一语不合于古音,及至城廓,则递相非笑。长沙诽曰:‘入浏阳门遇浏阳人,井呼浆,请呼抢……省呼想,影呼央,颈呼讲。’” [1]301邹氏根据自己的方言读音,定江摄的时音为古耕清青之正音。从音值的角度考察,邹氏的结论当然还可以再行讨论,但他批评长沙话中梗摄时音不合于古读,提出梗摄的古读与臻摄判然有别,“自不议合于真臻矣”,则为确论。
第二十一论考订蒸登部旧音。邹氏生活的时代,南音蒸登似真臻欣文魂,北音庚清青接近东冬钟。邹氏认为“二者皆非”,蒸登的旧音“实近之咍,殆与今之读咍韵无异,故与之咍通者十之八九”,并举方音为证。之咍与蒸登,实为同部异类。之咍为阴声韵,蒸登为阳声韵,阴声韵与阳声韵的相互转化,在传世文献及活语言中并不少见。这是语音发展的结果,“音节发音的响度大体上都是前强后弱,因而阳声韵、入声韵的韵尾容易因磨损而消失”[7]192。邹氏在此处以今律古,混同古音中阴声韵与阳声韵的界限,表现了他在审音方面的不足。周祖谟先生批评邹氏此书“不考本末、迷乱古今之论至多”,虽然严厉,但未失公允。
三. 邹汉勋古韵研究的特点
邹汉勋古韵研究的指导思想是“音有定数”。以传统哲学中的概念“数”为先导,进行古韵分部; 并以“数”为标准,评判传世文献与活语言的正误得失。合于“数”者则是之,不合于“数”者则非之。古音正韵十五类,合“五而三之”之数,再加上入声十类,亦合五五二十五类之数。邹氏认为:“夫等韵之摄,即古人之均部也。”然而邹氏所激赏者也只是《切韵指掌图》,因为该书共二十图,这是合于他的古韵十五类思想并且是合于“数”的——“宫声博而商稍隘,徵极隘; 宫声博,故可一类而二之。此二十部之所由分也” [1]305。至于《七音略》辖图四十三张,《切韵指南》创十六摄,四十三与十六皆不易从“数”的角度进行阐释,故概为邹氏所不取。
“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个形而上的宇宙术语。在生产力极低下的时代,古人对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多有臆测并盲目崇拜。数字符号附着先民的蒙昧意识,也被笼罩上了神秘色彩。《老子》第四十三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数”能化生万物并支配万物,这种思想在后世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宋代道学家邵雍即认为:天地所生万物均有既定的理数结构[8]。邹汉勋在构建自己古韵体系时,附会于理数,脱离语言事实,所得结论自然经不起验证。
将语涉玄虚的“数理”思想引入古韵部的研究,决定了邹汉勋采用的推理方式为演绎式。李葆嘉先生云:“(邹式古声纽研究的成果)似乎是从一个包罗古、今、汉、梵的二十声模式中推定出来的。”在古韵部研究中,邹氏也先验地确定了一个囊括古、今、雅、俗的十五类模式,然后,以此来分析先秦韵文、谐声材料、后世方音,并以古韵十五类为标准来检讨韵书、韵图得失。基于这样一种分析方法,邹氏不考虑《广韵》性质及功用,率尔批评其“不分大部类为失法”,并且提高“古人韵缓说”、“叶音说”的地位,认为他们与陈第的思想一样,应该视为研究古音的主要途径。后世的雅读与方音,凡合于古音十五类者,皆可成为例证,被邹氏采用; 凡不合者,则为其所不取,这又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要言之,邹氏研究古韵时以“数”导夫先路,这种胶柱鼓瑟的做法使他的古韵体系脱离了语言事实,成为玄而无根之谈。至于以活语言为材料,考订古韵部音值,邹氏启牖之功诚不可没。甚而至于,他对语音演变的认识已有离散式音变理论的萌芽。然而,他的考察范围局限于南楚方音,所得结果难免偏颇。时人将邹氏与江永、戴震相提并论,然而,在古韵研究方面,就方法的精审、结果的精当程度而言,邹氏实远不逮江戴二人。
注释:
① 郑贾:东汉经学家郑玄与贾逵; 江戴:清代音韵学名家江永与戴震。
② 何九盈、许良越等先生认为章炳麟是第一个对上古声纽有系统认识的学者,李葆嘉先生则认为清代中期的邹汉勋便已构设上古声纽体系,详细内容请参阅李葆嘉所著《清代古声纽学》。
-
表 1
上、急 中、缓 下、急 疾徐 宫 鱼模 歌戈麻 支佳 商 阳唐谈盐添严衔咸 东冬钟江侵覃凡 耕清青 角 真臻先 元寒桓删先 谆文欣魂痕 徵 脂皆 蒸登灰微 之咍齐 羽 宵萧肴豪 侯虞 尤幽 -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648
- HTML全文浏览量: 290
- PDF下载量: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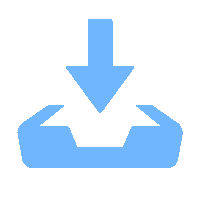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