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学术研究的“疑”与“通”——兼论郭沫若学术精神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
Skepticism and Maste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cademic Studies of Guo Moruo —His Academic Spirit and Its Consistency with Spirit of Shu Studies
-
摘要: 郭沫若一生学术研究,充满怀疑与变化,这既是他不惧权威、敢于独抒己见,融汇百家、打通古今中外,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诸特征与精神形成的内在动力,也是其建树丰硕、成为“球形”文化巨人的重要秘诀。当然,这也是郭沫若迄今为止遭受诸多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郭沫若的学术观念与研究方法,深受蜀学精神传统影响,显示出与后者本质属性的高度一致。Abstract: The academic career of the great Chinese writer, Guo Moruo, is full of incertitudes, which, in fact, are the expressions of his personality and scholar mentality. This feature makes it hard for some researchers to master his academic spirit. Based on in-depth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the writer and his comprehensiveness, this paper exerts itself to ease the skepticism and help master his greatness, concluding that his skepticism and scholar mentality much consists with those of the Shu Studies.
-
Keywords:
- Guo Moruo Academic Studies /
- skepticism /
- mastery /
- application /
- Shu Studies
-
郭沫若是中国近现代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奇特存在。尽管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一生功过是非依然争论未休,但郭沫若的学术成果赫然在世,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也不能从近现代史上一笔勾销。那些诋郭毁郭的人出于何种目的与动机,本文不去讨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郭沫若丰富多姿的人生是怎么形成的,他的学术成功,除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有力襄助,还与其生于斯长于斯的蜀文化土壤,有着怎样的内在关联。
一. 郭沫若早期学术研究的怀疑精神与融通观念
追溯郭沫若学术生涯,最早可算至1919年10月在日本所发表的《同文同种辩》,该文虽然被为郭沫若作简谱的卢正言称之为“时评”[1]18,但文章涉及中日两国的一些文化问题,具有一定学术性。1921年5月,《学艺》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刊发郭沫若关于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长篇论文《中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未完稿),从已经写成的部分,完全可以看出郭沫若学术研究的一些思维特征与方法理念,值得引起重视。在文章的序言部分,郭沫若认为中国三代以前的自由学术思想,悉被三代和秦汉以后的宗教迷信思想所堙没,他提出了恢复三代以前思想自由风气的明确学术主张:
吾人苟力屏去一切因袭之见,以我自由之精神直接与古人相印证时,犹能得其真相之一部而无疑虑。余即本此精神,从事发掘。所有据论典籍,非信其绝非伪托者,决不滥竽(原作“竿”,疑形近而误);后人笺注,非经附以批评的条件,亦决不妄事征引。在宿儒耆老视之,或不免有“自我作故”之讥,而在我个人,却是深深本诸良心之作。[2]68
在刚刚踏入学术领域的时候,郭沫若就显示了反对因袭、崇尚自由、追求真理的可贵独立与创造精神;对于历史典籍,坚持文献的可靠性原则,决不采用伪托的不可靠材料;对于后人的传注笺释,坚持批判性原则,没有经过严格审视和独立思考的学说或观点,决不妄加征引。他的这种精神和方法,对于数千年形成的传不破经、我注六经的学术传统思维与研究形式,无疑是鲜明的挑战,是宿儒耆老所不能容忍的。而在他看来,学术研究必须敢于怀疑、敢于突破、敢于创新、敢于坚持,才能发现真理,推动进步,他决心勇敢坚持这种对得起学术良知的探索与疑古精神。
1922年3月10日,郭沫若在日本福冈作《歌德对于自然科学之贡献》一文,对歌德的人生历程与学术路径作出了自己的解读与评价。文章开篇说:
吾人的精神活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美的直观的活动,一种是智的推理活动。依前者之作用而得种种的观感,其所表现则为艺术、为诗;依后者之作用而得种种之判断,其所表现则为科学、为散文。诗、学之分野,自不能混同为一如,然两者同属于吾人精神活动之产物,吾人如能等量而扩充与科,则两者自可兼能而并美。[3]86
在郭沫若看来,形象思维的艺术与抽象思维的科学,虽然按照学科知识划分为不同的门类,思维反应也有不同的方式,但它们都是人的精神活动产物,只要平衡兼顾,就可以发挥好两方面的思维作用,在不同研究领域取得成绩。事实上歌德就是这样的成功范例。他既在诗歌、小说、戏曲等姊妹艺术方面成为莫大的天才,又在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歌德一生,既领略了科学发现的快乐,又获得了艺术创造的满足。郭沫若动情地说:“吾人不能不敬仰歌德之天才,吾人不能不羡慕歌德之幸福!”[3]88郭沫若崇拜、羡慕歌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位兼具艺术与科学才能的天才,并且在不断求索创造中感受到了比常人更多更大的幸福。
在写成于1922年岁末、发表于1925年5月20日《创造周报》第2号的《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中,郭沫若特别推崇老子与孔子,其根本理由,就是认为老、孔二氏先后在春秋时期的动荡时代,敢于怀疑三代以来迷信鬼神的思想观念,树立起“动”而“通”的宇宙观和历史观。他评价老子说:“千有余年的黑暗之后,到了周之中叶,便于政治上与思想上都起了剧烈的动摇。一时以真的民众之力打倒王政,而激烈的诗人更疑到神的存在起来了。雄浑的鸡鸣之后,革命思想家老子便如太阳一般升出。他把三代的迷信思想全盘破坏,极端诅咒他律的伦理说,把人格神的观念连根都拔出来,而代之以‘道’之观念。”[4]256-257郭沫若称赞老子是革命思想家,原因就在于他敢于怀疑千余年间所迷信的人格神观念,是这种怀疑精神,使老子发明了“道”的本体概念,用它取代三代统治者推崇备至的人格神,从而在根本上破除了君权神授、替天行道的政治骗局。郭沫若一再表示自己崇拜孔子。他所崇拜的孔子,是一个兼有康德与歌德那样的伟大天才、圆满人格、永远有生命的巨人;是一个“要使人生也全能全智”的不断进取完善自我的完人;是一个“把自己的智能发挥到无限大,使与天地伟大的作用相比而无愧,终至于于神无多让的那样崇高的精神”的伟人[4]259-262。孔子是否被此时信奉泛神论思想的郭沫若美化和拔高姑且不论,我们从这里看到了郭沫若投射到孔子身上的一种观念与理想,那就是人的一生,必须不断追求进步和提高,直至止于至善而后已;人的智能之充实,必须不断地融汇已知,探索未知,臻于全智全能而后已。在郭沫若的思想观念中,懂得融会贯通既是一种拓展知识、提升智能、完善自我的主要方式,也是一种矢志不渝的人生态度与理想价值追求。
自郭沫若1914年初抵达日本到1924年11月从福冈回到上海,其在日本的10年多时间里,一直学习医学,最初在给家人的信中表达了“立志学医,无复他顾”的坚定选择[5]33,经过10年努力,他顺利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得了医学士学位。但自从国内五·四运动爆发以后,郭沫若的关注重点越来越转向政治,在文学创作上投入了几乎全部课余精力,甚至在课堂上也写他灵感勃发的新诗。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恰恰出现在他海外学医期间,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个结果,就连郭沫若自己恐怕也有些始料未及。但事情的结局,似乎验证了郭沫若在西贤歌德、古圣孔子身上观察到的客观事实:只要等量扩充人的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能力,就完全可以打通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能够在两大科学的各个领域有所作为。
1929年,郭沫若的史学代表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完稿,并于1930年由上海联合书店正式出版。该书不仅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对此后的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甫在1931年10月12日《大公报》上撰文称:“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要算是震动一时的名著。就大体看,他那独创的精神,崭新的见解,打破旧史学的乌烟瘴气,而为新史学开其先路的功绩,自值得我们的敬仰。”[6]3今天的研究者值得寻思的是,郭沫若刚由文学跨界进入史学领域,何以能够取得如此一鸣惊人的研究成果?郭沫若自己在1929年的该书“自序”中,给出了可信的解答:“我们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但这必要的条件是须要我们跳出一切成见的圈子。中国的社会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经二千多年,所有中国的社会史料,特别是关于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为历来御用学者所凐没、改造、曲解。”他进而提出要对包括胡适《中国哲学史纲》在内的诸多研究整理成果展开“批判”,明确批判的目的是要在“实是之中求其所以是”,“知其所以然”[7]6-7。显而易见,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获得的突破性成果,是其怀疑精神与独创精神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没有彻底摒弃旧史学因袭成见与落后方法的勇气,没有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察分析中国封建社会成败得失的眼光与见识,是根本不能办到的。
当郭沫若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候,陶希圣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郭沫若抱着很大的热情与期待找来阅读,读后大失所望。他对陶氏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和知识性错误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该书出现这些问题,原因之一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而其不能真正了解的主观原因,则是陶氏本人对古代社会历史研究的学科知识储备不足。郭沫若列举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材料有三方面的困难:第一,周以前的材料苦于少而难于接近;第二,周以后的材料苦于多而难于归纳;第三,周代的材料苦于伪而难于甄别。他认为,解决一、三两方面的困难,“非从考古学入手不可, 那须要你有地质学的知识,有古生物学的知识,有人种学、民俗学、金石文字学的知识”,“到周以后,那材料之多迳直是浩如烟海。‘九通’‘二十四史’乃至‘四库全书’以外的等量以上的书籍,此外还有未成书籍的史料,各种不成文法的民间的制度,民间的习俗,民间的口碑,以及露在地上的各种古迹,埋在地下的各种古迹,还有散失在海外的器物图书,等等等等”[8]184。仅就提及的这些学科知识和各种材料的准备,足见研究古代社会,没有通晓百科知识的本领,不具备融通取舍的能力,就难以得出客观科学、证据确凿的研究结论。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能够提出那些跟前人和时人不同的观点,除了研究方法的先进,注重甄别文献材料的真伪,主要得益于他在研究中大量采用了卜辞、青铜器铭文等地下出土材料,他称这是“现代考古者的最幸福的一件事”[9]6。正是感到考古成果对古代历史研究的极端重要性,郭沫若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致力于卜辞、器物铭文的研究,不仅在考古、甲金文研究领域卓然名家,而且在这方面的成果,大大有助于他后来对先秦诸子思想、先秦社会发展分期方面的研究,并由此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
二. 善“疑”会“通”造就了郭沫若的学术黄金时代
郭沫若一生的学术研究黄金期,无疑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的众多代表最高研究水平、并在相应领域对后来的研究产生广泛影响的成果,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为了说明问题,兹根据卢正言《郭沫若年谱简编》、肖斌如、邵华《郭沫若著译书目》(增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所系的各年著作出版情况,编制如下表 1:
时间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备注 1931 1.《甲骨文字研究》(上、下)
2.《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
3.《汤盘孔鼎之扬榷臣辰盉铭考释》
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
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上海大东书局
(同上)
北平燕京大学
上海神州国光社
翻译
(同上,未出版)1932 1.《两周金文辞大系》(线装)
2.《金文丛考》(线装四册)
3.《金文余释之余》(线装)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
(同上)手迹
(同上)
(同上)1933 1.《卜辞通纂》(线装四册)
2.《古代铭刻汇考》(线装三册)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手迹
(同上)1934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日本东京文求堂 手迹 1935 1.《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线装五册)
2.《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线装三册)
3.《日本短篇小说集》(芥川龙之介等著)
4.《生命之科学》(第二册)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
(同上)手迹
(同上)
翻译
(同上)1936 1.《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后半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2.《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3.《华伦斯太》(席勒著)
4.《隋唐燕乐调研究》(林谦三著)东京质文社
上海商务印书馆
上海生活书店
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
翻译
(同上)1937 1.《人类展望》(韦尔斯著)
2.《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线装五册)上海开明书店
日本东京文求堂翻译
手迹1938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言行出版社 翻译 1939 《石鼓文研究》(线装三册) 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周易的构成年代》 商务印书馆 1941 《屈原研究》 重庆群益出版社 1942 1.《赫曼与窦绿苔》(歌德著)
2.《屈原——五幕历史剧及其他》(含屈原研究论文9篇)重庆群林出版社
新华书店出版翻译 1943 《屈原研究》(新编) 重庆群益出版社 1944 《甲申三百年祭》 新华日报 1945 1.《青铜时代》(汇集30年代以来的古代研究论文)
2.《孔墨的批判》
3.《先秦学说述林》
4.《十批判书》重庆文治出版社
重庆群众周刊社
福建东南出版社
重庆群艺出版社1947 1.《艺术的真实》(马克思著)
2.《浮士德》(第二部,歌德著)
3.《历史人物》(汇集1941—1947年的历史人物研究论文)上海群益出版社
(同上)
上海海燕出版社翻译
(同上)在表 1所列内容中,未包括的郭沫若比较重要的学术成果,还有1952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编者新辑的《史学论集》,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整理、校订成果《管子集校》,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盐铁论〉读本》,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离骚今译》,以及1971年出版的郭沫若最后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李白与杜甫》。而《史学论集》编入郭沫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史学论文,其中一部分是写于三四十年代的,如《论儒家的发生》、《论古代社会》、《古代社会研究答客难》等。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20年,对中国的国内斗争和民族抗争而言,是十分特殊的,这种特殊时代背景直接影响到了郭沫若的人生命运。他旅居日本十年,是因为1927年蒋介石撕毁国共合作协议发动政变,拘捕共产党人,实行恐怖的独裁专制,导致大革命失败,郭沫若在国内无法安身,只得去海外避祸。1937年他回国,又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他必须回归故土参与抗日斗争,与祖国共存亡。从郭沫若在这近二十年间出版的学术成果可以看出,旅日期间他主要从事金石学、古文字学的研究,这期间其大部分著述几乎都是以手迹的形式由东京文求堂影印出版的。在回国之前,只有《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一文涉及先秦思想史研究内容。从1940年到1947年,他的研究重点明显转向先秦诸子思想、学说的考察比较,不同学派思想的传承发展关系,各家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身世、遭遇、政治分野、学术生涯等问题研究,并且试图对各家各派的思想贡献与历史作用按照统一标准进行准确定位和全面评判。显然他是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对古代社会形态与生产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之后,集中对古代的意识形态状况开展深入全面研究,在此基础上合观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面貌,以便完全看清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线索与轮廓,及其何以如此发展变化的深刻历史原因。
要实现这样的研究目标,无疑是难度极大且异常艰辛的。就拿在日本从事古文字学研究来说,条件相当受限。郭沫若在《我与考古学》中说:“我第二次跑来日本,手里是一本书籍也没有的。”[10]247文中谈到想买《殷墟书契·前编》,四册书要四百块大洋,着实让身为异国求学者的郭沫若吃惊不小,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购买财力。他转而想买《殷墟书契考释》,也是写信托上海的朋友买好寄去的。后来打听到东京上野图书馆藏有一部《殷墟书契》,他每天到图书馆阅读,直至读完全书。真正对他研究古文字学最有帮助的,是通过朋友关系,获得了到东洋文库去阅览所有甲骨文、金文库存书籍的机会,使他对甲金文的资料有了全面了解,并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严格说,郭沫若旅日期间的古文字学研究,是由此起步的。但研究的过程极其不易,他自己说过:“在日本亡命的那一段时期,有时候穷得来连毛笔也买不起。”[11]10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郭沫若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最关键在于其善疑会通。他在《〈甲骨文辨证〉序》中指出:“怀疑辨伪乃为学之基阶。为学与(其)失之过信,宁取乎多疑。子舆氏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终古不刊之论也。鼎彝甲骨诚多赝品,然而疑之有方,辨之有术,富有经验之士于其真伪之间几于一目可以别白。所贵于学者即在养蓄自己的目力,先期鉴别之精审,更进而求其高深。”[12]267 郭沫若认为,学问者,乃是从知识疑问产生,做学问的基础和方法,就是不断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所以他明确提出为学宁取多疑。当然,仅靠多疑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善疑,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到“疑之有方,辨之有术”,只有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最终成功解决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养蓄目力,鉴别精审,使自己有足够的鉴别力和判断力,让问题的解决沿着正确的途径不断前进,步步深化,进而达到高深的学术境界,解决重大学术难题。他还以甲骨文的识字为例,阐明善疑会通的道理:“识字有赖于师弟之传授,有赖于字书之检阅,固为经常之门径。然舍此以外不能谓遽无他途。盖人类有推理之智能,文辞有一定之轨迹。古文奇字不见于字书,虽无征于典献,苟非只字单文,率可由客观之论证,参验互雠而得……人患不知用心耳。苟知用心,有如国际侦探,虽密码电报亦有法破之,何况祖先所已曾使用之文字!”[12]268郭沫若所要阐明的道理在于,学问是有关联性的,解决一个学术问题,需要动用多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知识面越广,知识储备越丰富,就越有利于参验互雠,触类旁通,通过多种途径找到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与此同时,学术研究上追求真理的自信和勇气非常重要。郭沫若在众多研究领域能够取得引人注目的重要成就,与他性格中笃于自信、勇于追求真理的气质与特点密切相关。在甲骨文、金文研究过程中,他由最初的“门外汉”和没有一本专业书籍,到后来成为古文字学研究著名“四堂”之一,走出的成功道路令人惊叹。其秘诀之一,无疑应该归功于他的高度自信。他在《我与考古学》中说:“仅仅费了四五十天的工夫,把所有关于古器物文字之类的著作便完全读破了。在未读之前觉得有点可怕,被一些大人先生们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在一着手读之后,其实也只有那么一回事。”[10]248他敢于说四五十天“读破”所有古器物文字的著作,是因为原来被大人先生们说得神乎其神的东西,作为门外汉以为真是很神的高深学问,进入其中一探究竟,才发现并没有所谓专家吹嘘的那么神秘,也没有当初想象的那么高深。这样的信心坚定了他深入研究古文字的决心与勇气,短短数年间,他连续推出了十来种研究成果,并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权威之一的地位。
郭沫若追求真理的勇气,不仅表现在既有服善之心,又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学术观点,而当他发现了新证据建立新观点得出新结论时,敢于主动纠错,反思自己的阙失,检讨自己的错误。其《卜辞通纂·后记》对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成就极为推崇:“本书录就,已先后付印。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相示,已返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13]19董作宾最早提出甲骨断代的十大标准,对古文字研究及社会发展史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郭沫若对此认识清楚,非常佩服。但他也并不一味盲从,对于自认为正确的见解,敢于坚持。比如关于阳甲与沃甲的互易,帝乙迁沫事之有无,两人的观点就截然相反,郭沫若提出了自己所认定的证据与理由,用学术争鸣的方式提出商榷意见[13]21-26。
在郭沫若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面世之后,学界给予了很多赞誉,但他自己并未满足。自30年代初至40年代中叶,郭沫若又花了十五年时间对古代社会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1944年写成《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承认其过去在材料使用、历史分期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乃至得出了错误结论:“我在1930年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那部书,虽然博得了很多的读者,实在太草率、太性急了。其中有好些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一直到现在还留下相当深刻的影响。有的朋友还沿用着我的错误,有的则沿用着我错误的征引而又引到另一错误的判断。因此关于古代的面貌引起了许多新的混乱。这个责任,现在由我自己来清算,我想是应该的,也是颇合时宜的。”[9]3从言辞看,郭沫若态度非常真诚和理性,把因为自己研究的瑕疵造成学术混乱和消极影响的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没有推卸,没有狡辩。这种学术为公、追求真理、勇于承认错误的坦诚与勇气,十分难能可贵,在今天尤其值得大力倡导。
三. 郭沫若学术精神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
蜀学之源,一般追溯于西汉文帝末年文翁任蜀守时的兴学运动。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是时……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弟子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孝武帝皆征入,叔为博士。叔明天文、灾异,始作《春秋章句》。”[14]214据此,不仅蜀学之盛可以比肩齐鲁,而且官方立郡国之学,蜀实为倡首。更可值得注意的是,张宽(字叔文)学成以后,回到蜀中以教授学徒为业,倡导向学之风,取得了“变风为雅、道洽化迁”的明显效果;他同时治春秋学,成《春秋章句》十五万言[15]712。人们知道,《春秋》兼具经、史特征,且以现实实用性为取向,故孟子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张宽以天文、灾异说《春秋》,正是为了发挥其经世致用的特殊作用。其教学方式与治经方法,充分体现了文翁兴学、移风易俗的现实需要和实用目的。
自此以还,蜀中学风逐渐形成经、史并重,文、学兼修,通识博学,兼收并蓄的治学传统,以及通变致用,不拘成见,敢于质疑,笃于自信,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这种学术风格与特征,在一代代学者身上得以延续和彰显。比如扬雄,史称其“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用心于内,不求于外,于时人皆曶之;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16]3583在扬雄身上,能够看到许多蜀中学者共同的品质与精神,诸如以学术安身立命的人生价值观,治学不拘门户的博学贯通方法,敢于向经典挑战、不惧世人非议的自信与勇气,横跨经、史、文、辞多领域取得成就等。又比如三苏父子的文化观念与治学方法,其共同特点表现为文、史并重,“长于经济”[17]295,杂取百家,融会贯通。苏轼所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18]340,“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9]363,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最清楚表达。笔者曾指出三苏文化具有“观万物之全,明会通之道的文化包容性特征”,并进行了专门分析[20]4-6,此不赘述。只要我们深入研究三苏父子的治学历程和取得的学术成就,就不难看出其所具备的“全道”宇宙观、会通历史发展观和兼容并包、无所偏废的文化价值观。苏轼能够在众多人文和科学领域取得第一流的成就,成为彪炳史册的千古才人与文化巨匠,无疑是这种思想观念所玉成的。明代杨慎、近代廖平、直至现代郭沫若,蜀学精神一脉相承,清晰可见。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蜀学精神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不惧权威、敢于独抒己见的怀疑精神。郭沫若是伴随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局、观念大转变的特殊时代背景成长起来的。早年私塾教育,虽然以古代诗文等传统文化读物为主要内容,但其蒙师沈焕章思想并不陈腐,不仅鼓励郭沫若在读经诵诗之余阅读像《春秋左氏传》、《资治通鉴》、《东莱博议》一类的史书,引起郭沫若了解历史的莫大兴趣,且在其幼小心灵中,逐渐培养起他对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独特看法。1906年春,郭沫若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帅平均教授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古代经典的质疑兴趣,养成其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他自己说过:“我的好发议论的脾气,好做翻案文章的脾气,或者就是从这儿养成的罢。”[21]46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次社会变革与文化运动,“变法”、“革命”、“民主”、“科学”等层出不穷的观念更新,每每给思想观念形成过程中的郭沫若带来新的刺激和巨大影响。特别是郭沫若在乐山读小学、中学期间,先后受教于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两位高足帅平均、黄经华,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学术方法,对郭沫若此后的学术研究风格的形成,影响直接而深远。这一求学特殊经历,为郭沫若对几千年文明累积形成的既成定论和某些神圣经典学说产生怀疑和翻案的冲动,提供了丰饶的思想方法滋养。随着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接受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后,其在五四时期及以后创作的新诗中表现出的强烈“破坏”精神,及其这一阶段初步表现出在学术观念上对中国文明思想史发展轨迹的与众不同认识评价,集中彰显了郭沫若不为成见定论所圉,不惧权威、敢于独抒己见的怀疑精神。
第二,融汇百家、打通古今中外的致用精神。郭沫若接受西方文化,实际上几乎与私塾启蒙同步。在沈焕章为幼年郭沫若选择阅读内容时,《地球韵言》一类有关世界的知识,一并进入了郭沫若的学习范围。在他家的墙壁上,张挂了一张《东亚舆地全图》,郭沫若追述当时留下的印象:“红黄青绿的各种彩色,真是使我们的观感焕然一新。我们到这时才真正地把蒙发了的一样。”[21]45在小学学习期间,《启蒙画报》和地理、东西洋史等新式课程,是郭沫若十分喜爱的。稍后在日本留学的大哥经常寄回各种新潮知识读物,让郭沫若进一步拓展了知识视野,并表现出更多了解西方世界的渴望。1914年初,郭沫若经由天津、朝鲜渡海到达日本,开始长达10年的留学生活。虽然以医学为学业,但在课余时间,他大量阅读了古今中外的文化典籍,既有中国古代的、近现代的,也有欧洲、印度、日本、美国等世界各国的,涵盖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等诸多领域。从这一时期郭沫若撰写的《中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歌德对于自然科学之贡献》、《论中德文化书》等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视野是极为开阔的,学术观念是极为开放的,对于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遗产,秉持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开明态度。至三四十年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和先秦思想史,他的这种观念与方法表现得更为充分,取得的成就也愈加突出。郭沫若在1942年所作《关于“接受文学遗产”》中指出:
凡是文艺或文化的成品应该是无国界的。举凡先觉者的精神生产都应该是全人类共有的遗产,不仅固有的东西应当接受,既成的新旧译文应当接受,凡是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都应当赶快设法接受。[22]22
接受全人类所有有价值的遗产,目的在于为中国的社会进步、文化建设、文学艺术发展提供有益营养和借鉴启示。纵观郭沫若一生的道路选择与文艺、学术事业,其学以致用的宗旨与目的从来没有动摇过,改变过。台湾学者潘光哲评价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现实目的指出:“郭沫若倡言运用辩证唯物论(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社会的发展,或就中国历史、思想、社会的发展来考验马克思主义的适应度,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为后继者做了示范表演,实可视为另外一种表达政治意见的方式。”[23]郭沫若这种破除门户之见、古今界线、中外壁垒的继承弘扬文化遗产并为现实社会提供应用性借鉴的观念与做法,与蜀学精神高度一致,特别是与乡贤苏轼的文化观念十分相似,只要于我于世有用,博观杂取是没有任何条件限制的。显然,他们能够成为古今难得的“球形”文化巨人,与此密切相关。
第三,与时俱进、不断推陈出新的批判精神。郭沫若一生的学术道路,可以说是一直与“批判”二字相伴始终的。从《中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批判秦以后历代学者曲解三代思想,五四运动期间批判时流“打倒孔家店”、美化墨子兼爱非攻学说,到三四十年代批判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先秦诸子思想评价的各种观点主张,直至最后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依然旗帜鲜明地批判“千家注杜”的扬杜抑李评价倾向,他绝不人云亦云,显得与众不同。与“批判”用意殊途同归的是好做翻案文章。从早年为叛逆的女性翻案,到后来为众多历史人物如曹操、蔡文姬、李白、王安石、李岩等人翻案,他的见解都与史书描述的形象和作出的评价大为不同。在批判古今研究者学术观念方法及评价结论的同时,郭沫若从未放松对自己已有研究结论与学术成果的反省和自我批判,所持的观点也随着时代形势发展与自身认识改变而不断变化。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古代史分期观点的变化外,他对先秦社会形态、思想潮流、诸子流派的看法与评价,在不同时期也都不尽相同。根据笔者分别研究郭沫若对老子、孟子、惠施等人在不同时期的认识与评价,可看得尤为清楚[24][25]。郭沫若这种以攻击性姿态批判古今的做法,以及自身学术立场与研究结论的不断改变,既树敌甚多,又招致对手和今人的许多非议。有人别有用心地诋毁郭沫若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缺乏文人骨气。其实,人们只要深入考察一下郭沫若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他一生在关键时刻作出的重大人生选择,就不难明白他的学术研究价值取向和基本目的,完全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时事政治的需要。当他的思想立场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以后,他就毅然地严肃反省过去,改变已有思想观念。之所以如此,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说得非常明白:
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7]6
他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他也绝不固守明知不妥或过时的学术见解。为了创造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实现其立志报国的人生夙愿,他宁愿选择批判自我,否定过去,与时俱进,推陈出新。郭沫若这种学术观念与行为方式,同样深受蜀学精神的影响。唐宋以还的蜀中学人,都具有与时俱进、与时俱变的思想观念和学术特征,从唐代梓州赵蕤,宋代眉州三苏,到近代井研廖平,莫不如此。
-
时间 著作名称 出版社 备注 1931 1.《甲骨文字研究》(上、下)
2.《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上、下)
3.《汤盘孔鼎之扬榷臣辰盉铭考释》
4.《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
5.《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上海大东书局
(同上)
北平燕京大学
上海神州国光社
翻译
(同上,未出版)1932 1.《两周金文辞大系》(线装)
2.《金文丛考》(线装四册)
3.《金文余释之余》(线装)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
(同上)手迹
(同上)
(同上)1933 1.《卜辞通纂》(线装四册)
2.《古代铭刻汇考》(线装三册)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手迹
(同上)1934 《古代铭刻汇考续编》 日本东京文求堂 手迹 1935 1.《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线装五册)
2.《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线装三册)
3.《日本短篇小说集》(芥川龙之介等著)
4.《生命之科学》(第二册)日本东京文求堂
(同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
(同上)手迹
(同上)
翻译
(同上)1936 1.《艺术作品之真实性》(《神圣家族》后半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2.《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3.《华伦斯太》(席勒著)
4.《隋唐燕乐调研究》(林谦三著)东京质文社
上海商务印书馆
上海生活书店
上海商务印书馆翻译
翻译
(同上)1937 1.《人类展望》(韦尔斯著)
2.《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线装五册)上海开明书店
日本东京文求堂翻译
手迹1938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合著) 言行出版社 翻译 1939 《石鼓文研究》(线装三册) 长沙商务印书馆 1940 《周易的构成年代》 商务印书馆 1941 《屈原研究》 重庆群益出版社 1942 1.《赫曼与窦绿苔》(歌德著)
2.《屈原——五幕历史剧及其他》(含屈原研究论文9篇)重庆群林出版社
新华书店出版翻译 1943 《屈原研究》(新编) 重庆群益出版社 1944 《甲申三百年祭》 新华日报 1945 1.《青铜时代》(汇集30年代以来的古代研究论文)
2.《孔墨的批判》
3.《先秦学说述林》
4.《十批判书》重庆文治出版社
重庆群众周刊社
福建东南出版社
重庆群艺出版社1947 1.《艺术的真实》(马克思著)
2.《浮士德》(第二部,歌德著)
3.《历史人物》(汇集1941—1947年的历史人物研究论文)上海群益出版社
(同上)
上海海燕出版社翻译
(同上) -
计量
- 文章访问数: 858
- HTML全文浏览量: 315
- PDF下载量: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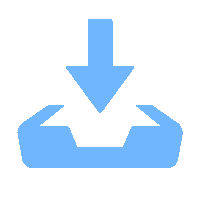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